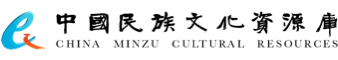

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依麻木镇国家通用语言学校的学生们在展示硬笔书法作品。乌什县委宣传部供图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回顾历史,自汉代正式成为中国版图一部分至今,新疆地区的历史始终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发展,新疆的命运始终与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考古研究表明,距今5300年前,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各地方文明在彼此竞争、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相互交流、相互借鉴,逐渐显现出一体化趋势。距今3800年前后,各地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最终融汇凝聚出以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其文化影响力。中原地区文化是中华文明总进程中的核心与引领者。此后,历经夏商周,大一统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秦汉两个统一封建王朝的建立,开创并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政治格局,大一统思想也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价值取向。自秦汉以来的2000多年中,中国历史上既有秦汉、隋唐、元明清的大一统时期,也有三国两晋南北朝、宋辽金的割据时代,但是每一次割据都孕育着更大规模的统一。无论是以汉族统治者为主还是以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主建立的王朝,无论是统一时期还是割据时期,大一统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从总体发展趋势看,新疆也是经历了从统一走向割据,再由割据走向统一的过程,这与整个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自公元前60年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新疆地区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无论是在国家大一统时期,还是在割据时期,新疆地区始终都在中央统一管辖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有效行使着对新疆地区的管辖和治理权,在新疆设立管理机构,派遣官员,驻扎军队,征收赋税,推行国家的法律等。这是新疆地区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方向。即使宋辽金时期新疆地区出现了如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国、于阗李氏王国,元代后期至清朝初期出现了东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准噶尔汗国等地方政权,但这正反映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各地区、各民族都处于不断交往交流交融之中。新疆历史上出现的割据局面,都是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一段插曲,是这一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我们不能仅用一个阶段历史的走势来否定长时段中作为主流的中国大一统格局。
先秦时期,古人常称国土疆域为“天下”“四方”,即古代国家的疆域是由中心(中原)、边缘(边疆)共同构成;在“天下”“四方”之中,其“国民”是由华夏(汉族)和四方的蛮、夷、戎、狄组成,也就是包括了华夏族(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组成了“五方之民”。正如唐玄宗时期一位士人杨若虚所说:“华夏者国之心腹,边陲者国之支体。若心腹克盈,则支体无害。”他将整个中国比喻为人的身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中原地区如同国家的心腹,而边疆地区则如同国家的肢体。如果心腹饱满,则肢体就没有任何损害。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是将中国的边疆地区视为整个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秦汉、隋唐、元明清等大一统时期,中央政权在新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长史府、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别失巴里、行尚书省、哈密卫、伊犁将军府等管理机构。而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宋辽金的割据时代,中原政权也始终对新疆地区实施着有效的管辖和治理。即使西域地区出现地方或割据政权,也都是我国疆域内的地方政权形式,都不是“独立的国家”。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外国文献及中国西北少数民族文献中,曾将古代中国称为“秦”。11世纪学者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将当时的中国分为上秦、中秦和下秦三部分。其中,上秦为北宋,中秦是辽朝,下秦为喀什噶尔一带,上秦、中秦、下秦三位一体为完整的秦。金元之际的李志常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称汉人为“桃花石”,相应在《突厥语大词典》的词条里,回鹘人被称为“塔特·桃花石”,也被直译为“中国回鹘人”。在喀喇汗王朝的钱币上,常有“桃花石·布格拉汗”“秦之王”以及“秦与东方之王”等称呼。这说明,即使在中国历史处于割据状态时,西域的地方政权喀喇汗王朝仍然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并没有自外于中国。比马赫穆德·喀什噶里时代稍晚的中亚人马卫集,在其《中国》一书中也称“中国这个王国地域辽阔,由众多城市、集镇、村庄所组成”,“他们的领土分为三个地区,即:秦、契丹、回鹘”。这说明,当时中亚地区的人们也普遍认为中国是由三部分组成,不仅包括了宋、辽,也包括了由回鹘人、葛逻禄人、样磨人等共同建立的喀喇汗王朝。
在古代中国,印是行使国家权力的象征。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汉朝统一西域后,对西域各地首领“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1953年出土于新疆新和县的“汉归义羌长”铜印,就是汉朝中央政权颁发给某支羌人部落首领的官印。据《魏略·西戎传》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车师后部王壹多杂被曹魏册封为“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王印”。明朝册封西域各地的首领为王,哈密、吐鲁番和瓦剌等地方首领都由朝廷册封,并颁发印信。据《明孝宗实录》记载,明孝宗在位时期,于1492年“诏哈密故忠顺王脱脱近属侄孙陕巴,袭封忠顺王,给赐金印、冠服”。1771年,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流域东归时,其首领渥巴锡见到伊犁将军,将明成祖于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颁赐给土尔扈特人的汉篆敕玉印献给了将军。这颗大印一直被土尔扈特人保存了360多年,表明其对中央政权的高度认同。新疆地区各民族首领接受中央政权颁赐的印信,表明自己是中央任命的地方官员,代表中央在地方行使权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自汉朝以后,历代中原王朝时强时弱,和西域的关系有疏有密,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管治时紧时松,但任何一个王朝都把西域视为故土,行使着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权。新疆地区各地方政权都有浓厚的中国一体意识,或认为自己是中原政权的分支,或臣属于中原政权。
正确认识新疆历史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然坚持使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话语。在这一话语体系下,我们对新疆历史的发展作出的结论就是,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开拓了中国的辽阔疆土,共同缔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当然,坚持将新疆地区的历史置于中国历史的构架下,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相关话语叙述其历史,并不妨碍我们将新疆区域性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置于亚洲史、东亚史、中亚史或内亚史,乃至全球史的视野下进行考察。但如果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将中国的边疆史、民族史、元史、清史等,从中国历史的叙事框架中剥离出来,仅仅强调它们的“内亚性”“中亚性”“民族性”“特殊性”“非中国性”,显然是在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来叙述中国历史,必然导致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割裂和肢解。更有一些西方敌对势力、境内外“三股势力”,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上,用“殖民性”“独立性”的话语解释新疆历史。在这一话语体系下,得出的必然是一系列谬论,并以此达到他们分裂、肢解中国的目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新疆地区的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新疆各族人民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始终与我们伟大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疆历史的研究和学习,必将带来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光明未来。
(作者系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