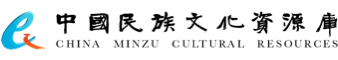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群舞《跳魁星》,回归了舞蹈的本质。周柔儿摄
人们普遍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舞蹈创作完全是两个层面的事情。非遗保护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非遗公约》)框架下,以政府为主导全面开展的保护工作;民族舞蹈创作则是舞蹈编导个人和个性化的创作行为。非遗保护需要尽可能地保留民族舞蹈的真谛,使其不被篡改和歪曲;民族舞蹈创作则必须尊重艺术创作规律,别出心裁、推陈出新,才能产生舞蹈佳作。
如此说来,非遗保护与民族舞蹈创作两者之间不仅泾渭分明,还互为矛盾:似乎非遗保护意味着“守旧”,舞蹈创作代表着“创新”。难道非遗是一成不变、毫无创新的吗?
《非遗公约》中明确指出,非遗是不断被“再创造”的。当然,这个“再创造”是有前提的,它是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因此“再创造”不是来自该群体以外的专家、学者、导演或是文化机构,而是非遗项目持有者自身的选择。传统舞蹈类非遗项目在不断地“再创造”中,吸纳了各族人民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必将为当代民族舞蹈创作持续地提供灵感来源。其实,不仅是传统舞蹈,非遗保护中所涉及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传统戏曲、民俗礼仪等,都为民族舞蹈创作提供了多样化的素材和形象。
因此,非遗保护与民族舞蹈创作,并不是二元对立关系。我国的非遗保护名录的十大门类中,传统舞蹈是其中一类。民族舞蹈是传统舞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非遗保护的对象。它与艺术家新创的民族舞蹈,共同构成了当代民族舞蹈的多维结构。况且,民族舞蹈的创新也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构建和发展的,否则舞种本身便不再具有民族性。从非遗保护的视角来看,将非遗转化为艺术创作的文化资源,是对非遗项目的“再利用”,也是对非遗的宣传和弘扬。
非遗保护这一文化思潮,为我国的民族舞蹈创作带来了新的理念,并产生了深远影响。譬如说,非遗保护的核心理念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陆续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骨干公约,如《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等。《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所提倡的是,所有文化具有同等尊严,并应受到同等尊重。该公约进一步指出,保护、促进和维护文化多样性是当代和后代的可持续发展一项基本要求。
近年来,随着非遗名录申报工作的开展,一些知名度不高的民族舞蹈的曝光率大为增加,改变了舞蹈界长期以来普遍重视汉、藏、蒙古、维吾尔、朝鲜等5个民族的舞蹈,而忽视了其他民族舞蹈。比如,汶川地震后,羌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后,羌族这个“云朵上的民族”受到世人瞩目,诞生了一系列舞蹈佳作,如《羌魂》《羌铃》《跳羌红》等。面对56个民族丰富的舞蹈资源,编导们大可多辟蹊径,通过创作使那些日渐被遗忘的民族舞蹈瑰宝“重见天日”。也只有更多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和边缘文化的舞蹈作品问世,才能改变民族舞蹈创作上选材单一的老问题。
此外,当前,非遗保护实践对传统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的珍视和呵护,促使舞蹈工作者开始反思其对待非遗传统舞蹈的态度。
我国非遗保护的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以“保护为主”的提法,扭转了我们以往对于非遗传统舞蹈单纯以“利用为主”的态度。长期以来,我们走进田间地头,用“以我为尊,为我所用”的方式采集舞蹈素材。当原有舞蹈动作难以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和编创者的思想情感表达时,创作者通过借鉴现代舞编舞技法,对原有动作素材进行拆解和重组。这种做法极大地丰富了舞蹈的动作和表现手法,但长此以往,创作者离乡土愈加遥远。尤其是很多舞者在城市中长大,在对民族舞蹈文化没有深入体认的情况下,用相似的编舞技法对动作进行重构,不仅破坏了民族舞蹈原有的风格、气质,也产生了严重的同质化倾向。面对如此情境,大家戏称是“现代舞惹的祸”。显然,现代舞只是“代人受过”,实为创作者们对传统舞蹈不够尊重、不够珍视、缺乏文化自信所致。
时下,越来越多的舞蹈工作者意识到,民族舞蹈的发展不能以丢掉文化传统为代价。在这样的“幡然醒悟”后,舞台上出现了《跳魁星》《打阿嘎》等一批与民俗生活更为贴近、动作编排更为质朴的舞蹈作品。又比如,北京舞蹈学院的《沉香》系列演出,舞蹈专业的师生们不只将传统舞蹈视为创作素材,而是将自己定位为传统舞蹈的继承者,学习并尊重传统舞蹈动作及其背后的文化特性。
无疑,当代的民族舞蹈创作,用背离传统的方式发展创新,还是用面向传统的方式发展创新,定然会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样貌。这应该就是非遗保护对民族舞蹈创作的意义之所在。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田青先生所说:“记住昨天是为了更好的明天。”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