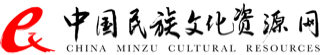历史上的河西走廊与中国西北疆域
“历史上的河西走廊在中国西北疆域形成的过程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河西经略与西域经略唇齿相连,没有河西走廊就没有西域,失去河西走廊的支撑,中央王朝难以治理好西域。汉武帝始设河西四郡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对多民族大一统的中国疆域的形成具有深远意义。河西走廊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东西之间的商业贸易为河西走廊带来了繁荣兴盛,在海上丝绸之路尚未开通前,河西走廊是中华文明与世界交流的主要通道。河西走廊还是诸多民族往来迁徙、交流交融之地,各民族共同开发了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安危对于关陇地区十分重要,所谓河西安则关陇安。河西走廊关乎国家经略,为中国的疆域形成贡献了重要力量。
河西走廊在中国西北疆域的形成中,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中央王朝对河西走廊的开拓,始自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此后经三国、两晋、北朝、隋、唐、宋、西夏、元、明各朝,河西走廊行政区及郡县名称屡有变动。降至清代,设凉州、甘州两府和肃州、安西两直隶州。今日河西走廊包括武威、张掖、酒泉、金昌、嘉峪关五市,面积27万平方千米,居住着汉族、藏族、蒙古族、裕固族、哈萨克族等众多民族。
从地理上看,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古玉门关(今甘肃、新疆交界处)。南北介于南山(祁连山和阿尔金山)和北山(马鬃山、合黎山、龙首山)之间,长约900千米,宽数千米至近百千米,为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平地,形如走廊,因位于黄河以西,故称河西走廊,亦称甘肃走廊。河西走廊的南面是连绵高耸的祁连山脉,海拔一般在3000—4500米以上,终年白雪皑皑,跋涉十分艰难;北面的北山山脉,属阿拉善—北山地台边缘的隆起地带,地势较南山低平,但处在蒙古高原边缘,外连渺无人烟的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行走极为不便。位于武威市的乌鞘岭是东亚季风到达的最西端。这里既是陇中高原和河西走廊的天然分界线,又是中国大陆半干旱区向干旱区过渡的分界线。
受周边环境影响,河西走廊沿途沙漠、戈壁和绿洲断续相接,气候干燥,冷热变化剧烈,风大沙多,年降水量只有200毫米左右。河西走廊的水系主要为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三大内流水系,均发源于祁连山,由冰雪融化水和雨水补给,冬季普遍结冰。依靠雪水灌溉使得走廊全境农业一向发达,形成典型的绿洲生态农业。古人云:“终岁雨泽颇少,雷亦稀闻,惟赖南山融雪回合诸泉流入大河,分筑渠坝,引灌地亩,农人亦不以无雨为忧”。河西走廊的张掖、武威素有“金张掖、银武威”之美誉。
就是这样一片富饶的土地,如何成为中国版图的组成部分,又在中国西北疆域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何等作用?笔者试图研讨论述,以求抛砖引玉。
一、开疆拓土中的河西四郡
进军并开发河西走廊是汉武帝锐意经营西北的第一步,它拉开了中央王朝向西域进发的序幕,尤其是河西四郡的设置,为多民族大一统的中国疆域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并非一蹴而就,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设武威郡、酒泉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张掖郡,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设敦煌郡,加之元鼎或元封中(公元前116年—前105年)在敦煌郡以西设置的阳关和玉门关,史称“列四郡,据两关”。
提起河西走廊,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内地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但汉武帝最初并不是为了打通西域而开拓河西走廊。实际上,西汉前期,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控制西域地区,它包括今天的河西走廊与新疆等地,匈奴在此设有西域王,并不断进犯中原地区。如元狩二年,汉武帝嘉奖骠骑之功曰:“骠骑将军去病率师攻匈奴西域王浑邪……降异国之王三十二人……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因其故俗,为属国”。又“是岁汉遣骠骑破匈奴西域数万人,至祁连山。其明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域”。
汉武帝在河西走廊采取一系列军事和政治措施,其最初动机并不是为了扩充疆域,而是为了反击匈奴以及出兵阻隔匈奴与西羌的联络。扩充疆域是果,不是因。
就匈奴一方而言,在匈奴头曼单于掌权时期,月氏是游牧在河西走廊的强大民族,居住在“凉、甘、肃、延、沙等州地”。此时的匈奴因受到月氏、休屠、浑邪等部的阻碍,尚未称霸河西走廊。头曼单于之后的冒顿单于被誉为匈奴的“一代天骄”,在他的带领下,游牧于河西走廊的休屠、浑邪部先后被征服,史称“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汉文帝时,匈奴进一步西进,接连破月氏,定楼兰、乌孙、呼竭及旁二十六国,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其领地的西部直对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乌孙,包括今河西走廊及今新疆在内的大部分地区。
汉武帝发起了对匈奴的持续军事进攻。元狩年间,遣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其后骠骑将军又出陇西、北地二千里,过居延,攻祁连山。在汉朝军队的不断打击下,曾臣服于匈奴的浑邪王率浑邪与休屠部四万余众归附汉武帝。匈奴在河西走廊的统治出现真空。汉武帝趁势进军河西走廊,在内地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先后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这是汉、匈交战以来,汉王朝获得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成果。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中原农耕民族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峙、冲突中,即使大获全胜,最终的落脚点大多还是回归到防御上,较少以攻城掠地为最终目标,所谓“且得匈奴地,泽卤,非可居也”。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大多也是以攻为守,而不是追求拓土扩疆。然而河西走廊的开拓却是少有的例外,它不仅实现了军事胜利,而且促成了中原农耕文明向河西走廊的延伸,扩大了中央王朝的疆域,其主要原因自然得力于祁连山雪水融化培育出的宜农宜牧的绿洲生态环境。
所以,汉武帝在“断匈奴右臂”后,很快将经营河西提上日程,先后设置河西四郡,驻官护守,将大批中原移民迁徙至河西走廊,戍边屯田,开发河西走廊,致使河西走廊的人口不断增涨。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东汉时河西四郡已有民户71000多,人口28万余,与内地郡县别无二致。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走廊成为儒家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域,创造出灿烂的五凉文化,著名的敦煌艺术就是河西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交融的产物。经过长期发展,盛唐时,河西走廊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走廊内四大城市的人口少则四五十万,多则二三百万。当时敦煌人口有百万之多,武威人口达到六七十万。唐代河西走廊的兴盛也带动了绿洲丝绸之路的繁荣。到了今天,河西走廊早已成为甘肃省最主要的商品粮基地和人口密集的地方。
历史表明,汉武帝为征讨匈奴而设河西四郡,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而言,其影响早已超出汉王朝,而成为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特别是在西域成为西汉王朝行政管辖区域之后,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和历史地位尤显突出。将河西走廊视作大一统中国的一部分,普遍成为历代中央政权固有的意识。
河西走廊处于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的接合地带,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如果不能控制好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各方势力的影响,河西走廊的防御便会十分脆弱。两千年来,中央王朝为保证这一通道的畅通,阻隔河西走廊南北各民族之间的联合,曾与当地少数民族政权反复争夺。
汉武帝是这一战略的肇始者。霍去病进军河西走廊之前,这里曾驻牧着众多的游牧人群,主要有匈奴、月氏、乌孙、休屠、浑邪、羌、氐等,其中的羌、氐等人群便是来自青藏高原。羌人除活动于黄河上游的河湟地区外,也有众多部落分布在河西走廊,如从祁连山进入河西的卯羌,曾经游牧于弱水(今黑河)流域的婼羌以及原居于祁连山谷,后出扁都口进入河西的羌人等。月氏最早与河西走廊的羌、氐等民族毗邻而牧,被匈奴打败后,大部分西迁,剩下的月氏人留在祁连山一带与当地羌人通婚生息,被称为小月氏。小月氏“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这些民族尽管语言、文化不尽相同,但游牧民族的共性又使得他们很容易联合起来,这种联合对于中央王朝是巨大威胁。汉武帝为此果断进军河西走廊,基本阻断了匈奴与羌、氐等民族的联合,使来自南北两个方向的威胁大为减弱。这一战略决策不仅维护了河西走廊的安定,也为此后进军西域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的这一战略决策被后来的很多王朝奉为巩固中国西北疆域的战略真髓。如隋朝建立后,主要军事压力一度来自雄踞于河西走廊南北的吐谷浑与突厥。突厥骑兵曾从固原进掠武威、金城等地。隋文帝运用“远交近攻,离强和弱”的策略,迫使突厥内讧、分裂,解除了北边突厥的军事威胁;接着又制服南边的吐谷浑。在经过几百年的动荡割据后,河西走廊又重新赢得了安宁。隋末,武威人李轨利用天下混乱的形势,割据一方,建立大凉政权,试图以河西走廊为根基与李唐政权一争高下。李世民荡平薛举的西秦政权后,李轨政权内部混乱,人心不稳,最终被部下安修仁擒获,送往长安处死。李世民以凉州总管进据河西,管理甘凉九州,河西走廊由此畅通。唐朝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得以大举进军西域。
河西走廊打通后,对于南北两个地域也呈现出较大的威慑与辐射作用。如西汉后期的名将赵充国,出兵平定河湟一带的羌人,进一步开拓河湟地区,就是得力于河西四郡的设置,反过来这些举措又进一步巩固了河西走廊的安全。
在历朝历代开拓和经营河西走廊的历史进程中,农耕人群和游牧人群的交流互补、迁徙汇聚、冲突融合,是推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也体现出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独特优势。
二、河西走廊与西域的开拓
从汉代到清代中晚期,包括新疆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被统称为西域。《汉书·西域传序》载:“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和准格尔盆地的边缘,人们利用高山融化的雪水在绿洲生活。包括塔里木河在内的诸多内流河及其形成的尾闾湖共同构成了西域地区农业与生活的主要水源,该区域城邦的兴旺与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据考古学家判断,楼兰即是由于河流改道与罗布泊的迁移而消失的。
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西域成为几大文明的交汇地和交通要道,“西域文明”所指,正是在世界四大古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之间产生的文明,其中有以塞人文化为代表的来自西方的欧洲文明,有以佛教为代表的来自南亚的印度文明,有以蒙古文化为代表的来自北亚的游牧文明。以贸易者和游牧人群为中介,西域与中原之间的交往早在商朝就已存在。于阗(今中国新疆和田县附近)出产的和田玉在商朝帝王武丁之妻的坟茔中被发掘出来,说明早在公元前13世纪东西方之间就已存在着商贸往来。中原地区的小麦等大量农作物的种植技术也是从西域传播来的。
西域复杂的自然环境孕育出多种形态的生计方式,形成了以游牧为主的城邦诸国和广阔的农耕区域。其农耕区域为汉朝军队进入西域提供了坚实的落脚点和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从而将黄河农耕文化与西域农耕文化连接在一起。汉朝因攻打匈奴而进入西域,并很快将经营西域作为战略选择。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控制东天山北麓的匈奴日逐王降汉,西汉统一西域。同年,西汉设立了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军政机构。这是中央王朝在西域设立的第一个行政机构,管辖范围已超出三十六国,标志着天山南北自此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与河西四郡的设置一道成为多民族大一统的中国疆域形成过程中的里程碑。《汉书·西域传》载,东汉时西域分裂为五十余国,但中央王朝对于西域的管理仍沿袭西汉的模式。东汉末年,西域各国相互之间不断兼并,至晋朝初年形成了鄯善、车师等几大国并起的局面。南北朝时期,西域局势再度变化,新兴的高昌国相继击败西域诸国,建立了一个地跨新疆大部的强国。除少数城邦国家外,西域诸国举国西迁,这一历史过程为中亚地区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十六国当中后凉的建立者吕光在统一西域后,依然仿效汉代,设置西域大都护,行使统治权。唐朝在西域设有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清朝设伊犁将军等机构管辖新疆。
对西域的开拓与经营,使得河西走廊的重要性陡然上升。河西走廊西连新疆、东系关中、南结青海、北邻蒙古,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西域都绕不开河西走廊,而中央王朝庞大的西域驻军则直接受制于河西走廊的物资供应。所以,欲图经略西域的中央王朝,出于政治、军事的考虑,均把河西走廊的开发与治理提升到保障国家安全、疆域完整的战略高度。
比如,唐代前期,由于中央王朝牢牢控制着河西走廊,故而在向西的战略上拥有极强的主动性。如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唐朝设河西节度使,驻守在武威,统率大军73000余,马匹18000余,担负着北御突厥、南防吐蕃的艰巨任务。河西节度使是唐代十大节度使之一,管辖范围包括凉、甘、伊、瓜、沙、肃、西等七州,即今甘肃西部与青海北部地区。这个地区用今天的话来说,是“点多线长”,故此河西节度使统帅的近两万名骑兵,时刻巡逻在各关隘、哨卡之间,守护着河西走廊与西域的安定。安史之乱后,唐朝开始衰落,吐蕃越过昆仑山北进,侵占了西域大部;中国北方地区也是战火连年,而西域与内地商人为求自保更是不愿穿行河西走廊,西域遂脱离中央王朝的实际控制。由此可见,河西走廊不仅是巩固西北边防、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的重要依托,而且对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除了作为中央王朝通向西域的政治大命脉,河西走廊还承担着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从历史上看,尽管东来西去的“丝绸之路”按其走向可分为好几条线路,但相对而言河西走廊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主干道,最为畅通、便捷、安全,并以张掖、敦煌作为东西方贸易的主要集散地。从长安出发后的北路、中路和南路,大多在张掖汇合,而分道西行的丝绸之路又以敦煌为起点,这绝非偶然,而是由河西走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社会状况等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从西汉到唐末,河西走廊曾经是“使者相望于道”,穿梭于河西走廊的中外商团为河西走廊带来兴旺繁荣。商业与戍边成为河西走廊各城镇生存与发展的两大基石。在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前,河西走廊成为中华文明与世界相沟通的必经之路。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尼雅古城,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在罗布泊北岸土垠汉代遗址,曾相继发现西汉王莽年间的汉简,这是目前已知的汉字在西域三十六国使用的最早记录。
通过“丝绸之路”,中原地区的农业、水利、冶铁、养蚕缫丝、火药制作、造纸等生产与科学技术以及丝麻织品、漆器、铁器与其他特色产品源源不断地传到西方。特别是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主要物品——丝织品,更是受到西方世界的青睐。古罗马学者普林尼在其所著《博物志》中说:“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妇裁成衣服,光辉夺目”。与此同时,西域和西方各国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也相继东来,大宛的汗血马、苜蓿、葡萄,印度的佛教、大秦的景教、波斯的摩尼教、拜火教,以及西域的小麦种植技术,胡豆、胡萝卜、蚕豆等农产品,琵琶、箜篌、胡笛、胡笳、舞蹈等等,也先后在大江南北安家落户,开花结果。
盛唐时,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敦煌是商旅云集的重镇,盛极一时。武威一度是陇右33州中最大的城市,有7个卫星城,住户十万余家,人口五十万余。这里经济发达,商贸极为兴盛,来自各地的“胡商贩客,日款塞下”,延续了长达数世纪的繁荣。数百年后,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他的《资治通鉴》中写道:“天下富庶者无出陇右”。岑参在天宝年间来到武威,留下了“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的千古名句。王维在武威写有众多诗篇,他的《凉州郊外游望》描述了当时凉州城外普通民众生活的情形:“野老才三户,边村少四邻。婆娑依里社,箫鼓赛田神。洒酒浇刍狗,焚香拜木人。女巫纷屡舞,罗袜自生尘”。在王维的诗中也反映了河西走廊多姿多彩的文化,他在《凉州赛神》中写道:“凉州城外少行人,百尺峰头望虏尘。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白居易笔下的《西凉伎》中“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贴齿……”也同样描绘了这种来自西方遥远之地的舞狮之风。而如今,白居易笔下的舞狮习俗依旧在河西走廊、永登一带流传。唐朝时,丝绸之路上大批粟特商人聚集在河西走廊,修建了他们的聚落,而唐朝政府也选取粟特人的大型商队首领(萨宝)为当地管理粟特事务的官员。据记载,仅敦煌一个乡就有粟特人约1500人,这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藏经中均有记录。河西走廊还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主要通道之一,至今仍在中外伊斯兰教交流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从这一点看,中央王朝对于河西走廊的经营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繁荣、为民族间的交往互动打开了通道,作出了重大贡献。
唐代途经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有多条支线,唐初突厥、吐谷浑曾严重威胁丝绸之路的安全。为此,玄奘大师西行取经,选择了丝绸之路南线,经天水、临洮、兰州,翻越乌鞘岭,抵达武威一线。等到玄奘大师取经东返时,突厥人的威胁已经解除,玄奘大师的东归路线则是从武威到景泰,过黄河,走靖远,沿萧关道回长安。玄奘大师东归的线路与著名诗人王维西行的路线大体一致。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王维从长安出发,沿着丝绸之路的北线而行,经泾川、平凉,绕六盘山西行至宁夏固原(即萧关),然后沿萧关道入靖远,直抵黄河岸边,渡黄河进入景泰,然后经古浪、大靖、土门入武威,这是当时长安通往西域最为便捷的一条道路。
到了成吉思汗时代和元王朝时期,整个中亚和东亚又被重新连接起来,海上和路上丝绸之路同时并进,当时贸易极为繁盛。中国的丝绸贩运到欧洲,价格猛涨几十倍。
元以后,大一统王朝走向割据状态,导致通过河西走廊的丝绸、瓷器、香料贸易急剧萎缩,至明代后期,由于封关闭国,陆上丝绸之路几近停滞。再加上地理大发现开辟了新航线,海洋转而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通道,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大幅下降。
总体而言,河西走廊历史上曾是中原通往西域、中亚、西亚以至非、欧的必经孔道,也是历代中原王朝在势力强盛时锐意经营西域道路上的重要中继站。河西走廊连接中原和西域的重要性,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有着全方位的体现。对河西走廊的历史作用的准确理解,是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疆域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形成过程的重要前提。
三、河西走廊与关陇安危
从东西方向看,河西走廊非常接近关陇,从乌鞘岭—天水一线到咸阳—西安(长安)只有350千米,所以对于关陇而言,河西走廊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其成为维护关陇稳定的重要屏障。明代名臣杨一清曾言:“兵粮有备则河西安。河西安则关陕安,而中原安矣”。对于扎根于关中的王朝而言,河西走廊的安稳尤为重要。关中王朝如果失去西域,陇右、河西则门户洞开,强大的游牧民族就会一路闯进关中,进逼长安,所谓“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
东汉末年,凉州羌患不断,直接威胁关中,东汉朝廷不得不花费大量钱财兵力才得以保住关中。安史之乱后,河西节度使的兵力被调往东部平叛,河西走廊空虚,吐蕃人乘机攻占河西走廊,河西与中央王朝的联系遭到了极大削弱。河西走廊丢失后,唐王朝只能困守陇山以东与吐蕃等进行长期的拉锯争夺。吐蕃骑兵距长安只有一两天的路程,唐朝因此极其被动,这也是导致唐王朝后期一蹶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
北宋时期,河西为西夏政权所有,宋朝失去了军马的重要产地,致使在与辽、金、西夏等政权对抗时毫无优势可言。与此相对,少数民族政权如西夏在据有汉化程度较高的河西走廊后,文明程度迅速提升,成为与辽、宋三足鼎立的一方势力,而河西走廊也因此成为西夏的核心区域之一。
明清时期的藏族和蒙古族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对河西走廊产生重大影响。清初,准格尔部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以及和硕特汗国的罗卜藏丹津等蒙古贵族先后起事,使得北到外蒙古、西到新疆、南到西藏的广大地区长期处于战乱状态之中,这对于关陇地区乃至清政府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在平定西北战乱、统一新疆的过程中,河西走廊同样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所以,清朝顾祖禹强调:“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这样一种军事地理的空间结构,对于我们思考今天的中国问题同样有着深远意义。中原、河西、西域,三者浑然一体的密切关系,不啻是个鲜活例证。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中国的多元亚区域之间,如何能够形成内在的有机关联,从而历史性地融为一体;另一方面,也展现出在融为一体的过程中,河西走廊所发挥的重要媒介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河西走廊成为了我们理解“何谓中国”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作者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