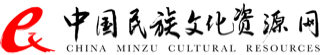芦笙吹响的时候

婀娜多姿的拉祜族芦笙舞。 资料图片
上世纪50年代初,居住在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佤山的佤族人、拉祜族人,几乎还采用原始的刀耕火种生产方式。每年雨季过后,他们便砍倒一片片山林,一把火将其烧净。经过一番风吹日晒之后,青绿的坡地上剩下一层厚厚的的灰烬,人们就在火灰上种点旱谷。由于靠天吃饭,收获的粮食少得可怜,佤族人、拉祜人常年处于饥饿之中。
1952年冬,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一一五团二营进驻西盟佤山,很快组成多个民族工作组分赴各个村寨,担负起政权建立前的一切工作,并动员当地群众利用山高水长的特点开垦水田。
出生于江西省鄱阳县的彭荆风走在了这支队伍里。彭荆风在新中国成立前读过两年初中,因家贫失学进报社当了学徒,后来靠自学校对,当上了记者和副刊编辑。1949年6月,他在南昌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了云南。
彭荆风和战友们走进村寨,见到的是多年没有修葺、枯朽的茅草顶和破烂的竹篾墙。不少人家连锄头都没有,只能用长刀砍地,用木制梭镖点播谷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解放军动员佤族头人、拉祜族头人去有了新气象的勐朗坝参观学习。
勐朗坝古时本是一个人烟稠密的地方,清代就有近万名傣族、拉祜族、哈尼族人在坝子上居住耕作。但在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一场因镇压引起的民族仇杀和相继而来的大瘟疫,使得坝上的居民大部分死亡或逃走,昔日富饶的坝子成了人间地狱。“要下勐朗坝,先把老婆嫁”,人们提到这个坝子就谈虎色变,唯恐避之不及。解放大军于1950年移驻勐朗坝之后,消灭了疟疾等传染病,人们不断迁入,勐朗坝重现生机。后来,澜沧县以此作为县城所在地。
跟勐朗坝一样,还有一个满是“鬼魅之气”的广缅坝子,也是从过去的繁华到“万户萧疏鬼唱歌”。狭长的坝子上,水田全都荒废,遗留的田塍水沟蛇虫横行,落叶荒草形成的腐蚀质土有一两尺厚。人们曾看到,无比珍贵的树下泉眼全被枯叶遮盖,湿地上全是杂乱的野猪蹄印。四周弥漫着潮湿白雾,长着不同种类的黄芭蕉、灰芭蕉、绿芭蕉,毛色金红的猴子在两三人合抱粗的大榕树、木棉树上蹦跳——这就是当年云南澜沧、西盟一带的情形。
解放军组成小分队,年轻的战士们和山寨里的拉祜族青年,一起到坝子上重新开垦田地,将那些荒废的水田重新灌水栽种。他们手足相依,战士们吃着拉祜人的冷饭团、竹筒饭和辣子;拉祜人吃着战士们的罐头,喝着他们的大叶茶。他们一起挖灰姜苗和野葱,一起唱树叶调、对歌。月光下,他们在一个窝棚里过夜,在那片一两百年来都没住过人的地方燃起篝火,在火中投放采摘来的草药,提防身子大得如细长蚂蚱的蚊子。他们在火堆边烤火聊天熬夜,实在困乏了,才进窝棚里躺一小会儿。他们夜里总是睡不安稳——草丛里有一种细小得如灰尘的“辣蚂蚁”,闻着人的气味就会爬过来,叮得人皮肤上如同涂了辣椒水一样火辣剧痛。
深夜里,睡不着觉的战士们常在月光下看见一些小黑点悄悄从山脚下的树林向坝子边上的小溪移动。开始,这景象让人有些紧张,后来才弄明白,原来是母麂子带着小麂子从山上下来喝水。战士们抱着枪一动也不敢动,生怕惊动了它们。
在他们一天天的耕耘下,坝子上百年的“鬼气”一点点散去。清早,鸟雀开始嘹亮地鸣叫,毛色金黄的画眉鸟、灰色的过山雀从树林里飞起,展开翅膀在白雾弥漫的坝子上盘旋飞翔。小河边有了俊俏的姑娘洗脸梳头,那长过腰身的头发柔软漆黑。芦笙开始吹响,多情的心上人有了幽会。
“从前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彭荆风将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变成了文字,记录下了云南边疆几十年走过的路程。当年,他写过“广缅坝子”调查报告及进一步的申请,上级批复:“这是大好事,要全力支持。由工委拨一笔钱给老乡们买锄头、斧头、粮食、种子。人力不够由驻力索寨的第五连尽力支援,药品请防疫队拨给……”彭荆风和战友们在八嘎那寨开水田,第二年春夏犁田插秧,秋后获得丰收。佤族人、拉祜人不仅留足了一年的口粮、种子,还用卖余粮的钱还清了欠账。他们抢着给解放军送来新米,还有背篓大的冬瓜。
我来到《民族文学》工作的2006年春天,在杂志的版权页上看到编委会成员名单,那是由蒙古、藏、维吾尔等多个民族的作家、编辑构成的,云南军旅作家彭荆风是唯一的汉族编委。知道彭老的文学经历之后,我好生惊叹,他曾写出一系列边疆小说,并与人合作完成了电影《边寨烽火》和《芦笙恋歌》的剧本,电影风靡全国。那是我们儿时看过的电影,意想不到的故事,好听极了的歌声,让人一直回味。
我第一次见到彭老与他的女儿彭鸽子时,虽然早已听说他是一位性格顽强的老军人,但见面之后,仍然为他久经坎坷之后的淡定和对生活的饱满热情吃惊。他们父女总是面带微笑。彭老脖子上挎着一个相机,对一切新事物都抱有浓厚兴趣,而对自己经历的苦难却很少提及,仿佛都已随风而去。其实,沉默未必等于忘却,只是这位老军人已经锤炼得如钢似铁。听说彭老一直在埋头写作,2010年,他以50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解放大西南》一跃登上了鲁迅文学奖的金榜。这时,他已过80大寿,曾经为了精益求精而十易其稿。专家们评价:“《解放大西南》以雄浑开阔的笔触,全景式地展开了解放大西南的历史画面,是一部气势磅礴的作品,又是一部见微见妙的作品;从中我们看到了彭荆风经年累月的自觉积累、追求完美的创作态度。”
那年5月,我在襄阳又幸逢彭老,他去领取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一个奖项。他仍然是那样地淡定和热情,脸上满是阳光。我向他约稿,一个月之后,他就寄来了散文《告别刀耕火种——忆初进佤山》。这篇散文与电影《边寨烽火》《芦笙恋歌》都来自解放初期西南边境地区的真实历史,来自他珍藏已久的记忆。他的笔法轻灵却又沉甸甸的,作品记载着佤山拉祜人的历史,反映了解放军与兄弟民族相濡以沫的情深意长。
事实上,彭荆风所写到的佤族人、拉祜人生活的地方都处于我国的边境,西与缅甸为邻,距省会昆明却有近千公里。长长的国境线上一直战争不断,民不聊生,加上瘟疫不时流行,求医无望的百姓只有等死或是逃离家园。这样的情形,延续了几百年。杜甫的一首《闷》诗中写道:“瘴疠浮三蜀,风云暗百蛮。”云南相比蜀地,越加是林深草密、高温蒸郁,云南边疆因此成为人们望而生畏的瘴气之地,少有朝廷官员问津。直到1949年2月,迤南边区人民自卫军第一支队占领澜沧县,成立澜沧专员公署,后来又单独设立了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两个自治县如今都由普洱市管辖,那里生活着彝、白、拉祜、佤等多个民族。
如今,那片土地上早已是气象万千——那里的人们栽种谷物、豆类,还种茶叶、咖啡、甘蔗、橡胶树和核桃树,并建起了养生蔬菜基地和生猪标准化养殖场。他们栽种小树苗,期盼它们成林。他们办起学校,中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49%。当地农民获得了新农合医疗补偿,农村公路建设通村硬化项目正在不断实施……
或许,人们对今天那里的生活早已司空见惯,认为从来就是如此。但要是知道过去那里曾是一个充满瘴气的地方,没有稻谷只有荒芜,没有人烟只有孤魂野鬼,没有歌声只有兽嚎,人们或许才会对眼前的栽种、养殖、读书情景,甚至行走的道路倍感亲切,也才会明白,那一刻芦笙的奏响,是怎样地让人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