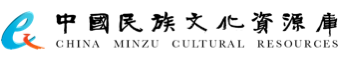

鄂温克人的家园

11月2日,迟子建在茅盾故乡接受颁奖

迟子建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11月2日,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在茅盾先生的故乡乌镇举行了颁奖典礼,黑龙江省著名女作家迟子建凭借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摘取殊荣,这也是26年来,东北三省作家获此殊荣的唯一一人。《额尔古纳河右岸》一书,将茅盾文学奖、迟子建与少数民族联系起来,并为鄂温克族的文化争得了尊重和关注。
听说迟子建
1964年,迟子建出生在黑龙江省最北方的小村“北极”。1983年开始,迟子建从事写作,至今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500余万字,出版40余部单行本。曾经从中国作协的朋友处听说过迟子建,说“她的笔触总不肯离开东北的老家,小说故事总是悲哀中不失温暖,屈辱中不失挣扎的力量”。
迟子建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以下简称(“《额》书”),小说集《逝川》、《雾月牛栏》、《清水洗尘》,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等,曾获得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茅盾文学奖作为全国性文学大奖,历来备受关注,读者称其“茅奖”,名称中流露着对一代文学大师茅盾的景仰。面对荣誉,据说迟子建在颁奖仪式以及过后的时间内一直保持低调,不愿接受采访,从此事也能感受到这位女作家内敛、温和的气质。获奖当天,当迟子建被问起《额》书如何能够从近4000部参评作品中脱颖而出,得到评委青睐的原因时,她说:“我想是作品里面所体现出的那种人性美吧。一个比较原始的部落在都市化进程当中,完好地保留下来我们之前所不熟悉的文化和传统,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神秘的,同时也是需要我们关注的原始之美。”
颁奖典礼上,在获奖感言的时间里,她说:“一个人也许不该记住荣誉的瞬间,但是在这个时刻我要坦诚地说,这个夜晚会留在我的记忆当中。因为我觉得跟我一起来到这个颁奖台的不仅仅是我,还有我的故乡,有森林、河流、清风、明月,是那一片土地给我的文学世界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由于城市化的进程和城市资本向乡村的流入,中国的乡村正发生着巨大和深刻的变化,身为一个农民的后代,迟子建热切地关注着这种变化。她说:“在我的故乡,这种变化使我的父辈、平辈和晚辈们既感到高兴和充满希望,又感到惶惑、不安和痛楚。为了表现出这种心态和心境,我写了这部书。”
《额》书与少数民族联系起来
相信一路读着迟子建的文字走过来的读者不难发现,她的写作随着其年龄的增长、人生阅历的丰富正渐入佳境,其最初的真诚与爽朗也并未因世故浸染与人生得失而褪色。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90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这样充满宿命色彩的句子,是《额》书带有魔幻味道的开头。
《额》书是我国第一部描述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迟子建以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自述口吻,将这个人口较少民族顽强的抗争和优美的爱情娓娓道来。小说语言精妙,以简约之美写活了一群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有媒体评价:“小说以小见大,写出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悲哀,其文学主题具有史诗品格与世界意义。”
小说带领人们走进了中国北部重要的界河——额尔古纳河,并且与生活在那里的孤傲而艰难的鄂温克人紧紧联系起来。额尔古纳河作为中俄两国界河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清朝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确定额尔古纳河为中俄界河。如今,河的左岸为俄罗斯联邦,河的右岸为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纬度最高的城市——额尔古纳市。
小说中,独特的 地域文化、神秘的民族风情背景下,众多血肉丰满的人物在此上演大起大落的悲喜剧。整部作品中,虽然超现实的元素并不鲜见,可字里行间晃动的都是作者对鄂温克这一古老民族或者说对我们现实世界的思考和隐忧,直指作者对生命、情感的体悟。读罢全书,萦绕在内心不易挥去的,多是忧虑和伤感。
《京华时报》评论说:打上浓重地域烙印的写作就同浸透少数民族特质的写作一样,很可能从当下文坛的主流庸常主题(都市、乡村、男女)中跳脱出来,何况《额》书既是地域的又是民族的。这当然不能算是一种取巧,事实上这样的“巧”并不好取,非得有丰厚的积累与平静的写作姿态才行。从这些年的创作轨迹中可以看出,迟子建具备上述取“巧”的两大要素。什么样的土壤孕育什么样的作家,常年偏居中国冰雪地带的迟子建在包括《额》书的诸多作品中呈现出有别于其他女作家的大气与爽朗,哪怕是属于女性的细腻、感性,也都往往透着宽广。
故乡与文学创作
从《伪满洲国》到《额》书,迟子建的作品无不浸透着她对历史的思考,当然这种对历史的思考不是孤立和割裂的,它与现实还是有着很大的关联。迟子建觉得,仅仅凭吊历史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能把历史作为“现实”来看待,作品才会有力量。《额》书虽然只有20多万字的篇幅,但里面讲述的却是鄂温克族的一个部落近100年的历史,而且舞台只有一座,那就是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森林。
迟子建说,可以用“悲凉”二字形容目睹这支部落生存现状时的心情。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以一些原始生活的永久消失和民间艺术的流失作为代价。我们为了心目中理想的文明生活,对我们认为落伍的生活方式大加鞭挞。现代人就像一个执拗的园丁,要把所有的树都修剪成一个模式,其结果是,一些树因过度的修剪而枯萎和死亡。其实真正的文明是没有新旧之别的,不能说我们加快了物质生活的进程,文明也跟着日新月异了。诚然,一些古老的生活方式需要改变,但我们在付诸行动的时候,一定不要采取连根拔起、生拉硬拽的方式。
作家苏童说,迟子建有一个先声夺人的故乡,具有写作题材上的先天优势。在早前接受《北京日报》记者采访时,迟子建曾经说,她最早就是想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在上学时就开始写日记,主要是写故乡熟悉的人、事和风景。“我出生在黑龙江漠河,故乡对我很重要,我的创作题材都出自这里。一个作家以一方水土资源为基础,可能创作上更便利。但再好的风景摆在那里,也要看人怎么去处理,缺乏后天的努力是没法写出好作品的。”
从迟子建的作品和她的生活经历中,可以看出她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浓郁的故土情结,她认为,没有大自然的滋养,没有她的故乡,也就不会有她的文学。迟子建的文学启蒙于故乡漫长的冬夜里外祖母所讲述的神话故事和四季风云骤然变幻带给人的伤感。她说,一个作家,心中最好是装有一片土地,这样不管你流浪到哪里,疲惫的心都会有一个可以休憩的地方。因此,在众声喧哗的文坛,迟子建才可以因为听了更多大自然的流水之音而不至于心浮气躁。有了故土,如同树有了根;而有了大自然,这树就会发芽。如果没有对大自然深深的依恋,迟子建也不会对行将退出山林的鄂温克的这支部落有特别的同情,也不可能写出《额》书。对迟子建而言,故乡和大自然是她文学世界的太阳和月亮,它们照亮和温暖了迟子建的写作和生活。
请关注鄂温克人
《额》书的主题是一个世界性话题,是关系到文化人类学的问题。这也是内蒙古社科院研究员、鄂温克族的白兰长期关注的问题。关于《额》书所传达的意义,白兰认为,《额》书关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小说更是对鄂温克人的族群和生活方式给予了极大尊重。她说,这可能跟迟子建的生活经历有关,她是在兴安岭长大的,虽然不是鄂温克族,但和鄂温克人有着相同感受。面对民族文化逐渐消失的事实,心中对于未来隐有担忧。
迟子建认为,人们不应以“大众”力量,把某一类人给“边缘化”,并且做出要挽救人于危崖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摆布他们。“如果一支部落消失了,我希望它完全是自然的因素,而不是人为的因素。大自然是美好的,也是残忍的。”
作为研究者,白兰读罢《额》书,与作者的共同感受,就是对文化、环境的迅速变迁的忧伤、哀愁,还有眷恋。白兰说,迟子建深知,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家园,她尊重文化精神,并愿意通过自己的笔触,引导读者的眼界穿越森林,寻访人与自然的核心价值。
鄂温克族作为一个人口较少民族,沉静、舒缓地生活着,它不为人知,不为人关注,《额》书的获奖,无疑形成了一种文化提示,它在叹息之余,更为鄂温克族的文化争得了尊重和关注。
专家评说
陈建功(中国作协副主席):
近几年国内的长篇小说比较关注现实生活,比如《秦腔》和《湖光山色》,都是在发现新的生活。有些作品注意对本土、民间资源的开掘,像《额尔古纳河右岸》里那种民族民俗的描写,鄂温克民族的风情描写都是很新颖的。
陈晓明(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题材与视角都比较独特,它关注的是一个很小的民族与群体,当然这一点并不能当做获奖的充分理由。除此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反映了这个民族在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中,不断进行抗争和抵抗的现实。这与当今世界文学的主题也是非常吻合的。
胡殷红 (中国作家网总编辑):
迟子建的作品中既有北方那种特有的长夜里的落寞、高远天空下的沉寂和漫长冬天里对春天的企盼,也有女性那种独特的、温婉细腻的心理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