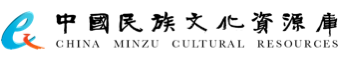
黎族是中国古老民族之一,海南岛的原住居民,自远古以来就在这片热土繁衍生息,开垦与建设祖国南疆,守护国土。黎族是我国所有文身的民族中,文身习俗最古老,持续时间最长,其形态、纹样保持得最完整和文化内涵最丰富的民族之一。
《山海经》是最早记载黎族纹身习俗的古籍,其文曰:“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郁水出湘陵南海。”文中的“雕题国”,指的是有纹身习俗的部落,据考证就位于海南岛,书中所记就是今黎族先民的纹身习俗。
黎族文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黎族母系氏族社会的遗存,体现了黎族自身的族源意识、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这些用血肉之躯展现出来的神秘图案,为黎族文化增添了斑斓色彩。黎族女性所纹的图案多种多样而又内含玄机,绘于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含义。
最重要的文刺部位是颊和颏,特别是颊部,几乎是每个纹身者必不可少的文刺部位。脸部两颊的纹图代表“福魂”,上唇的纹图代表“吉利”,下唇的纹图代表“多福”,手臂上的纹图代表“平安”,胸上的纹图,代表“财富、多子多福”,大腿上的纹图等代表“避邪护身”。

黎族妇女脸上刺黑纹
纹身颜料多用麻疯树籽灰拌水而成;也可以用螺壳灰、红槌树皮、蓝靛草等加水适量,发酵一个多月后制成;或用野生的黄豆叶、蓝靛草加水和小鱼虾等发酵而成;还有一种是用墨汁加几种野生草叶和树叶汁混合而成。
黎族女性纹身年龄一般都在“年将及笄”,即十三四岁即将成年之时。某些黎族女性纹身部位多、面积大,手术很难一次性完成,多按部位分数次,在几年内完成。
黎族女性纹身习俗是怎样形成的呢?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
在很久很久以前,海南岛五指山下冲山河边,有个番响寨,寨里有个姑娘,名叫邬珠,是五指山一带最美丽的姑娘。她说的话,听起来比蜜糖还甜;她唱的山歌,像溪水潺潺流;她弹的口弦,青鸠鸟也飞来相和。邬珠的手艺巧,能织天上的彩云,能织山中的凤凰,织成的筒裙啊,夜晚能放射金光。
菠萝蜜熟了,蜂蝶争着来采蜜;邬珠长大了,后生都想和她相交。五指山下的后生可多了,个个勤劳、善良,但是,真正配得上邬珠的,只有番空寨的帕昂。帕昂这小伙子,长得像椰子树那样挺拔,张开千斤弓,能射天边的飞鸟;点燃火药枪,能打狂奔着的野兽、后生们喜欢他,天天找他去打猎;娜邬(黎语,意即姑娘。)们喜欢他,夜夜邀他去寮房(黎族习俗,女儿长大了,父母替她在树边或山上搭起一间茅寮房,给她独居。夜晚,男女青年都喜欢聚在寮房里唱歌玩乐)。
邬珠与帕昂,很早就已经相爱了。当三月槟榔花开得最香的时候,他俩就定下了亲事,只待十月槟榔果红熟透时,邬珠就要嫁到帕昂家去,就要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帕昂为了在喜日那天能热闹一番,特意邀了几个相好的后生,背起猎枪、干粮,上山打猎去了。
五指山的秋天,常常会打台风,山外来的总管(旧时的官名,是朝廷的命官),尽给黎家做坏事!地里长出的庄稼,他要收一半;山里打来的猎物,也得送给他;他看上了那个娜邬,那个娜邬就毁了一生。
一天,总管带领官寨里的人马,出门去打猎,从太阳出山打到太阳落山,踏坏了多少青苗、偷去了多少苞麦,可是连个山猪也没有碰见。傍晚,他们从番响寨经过,看见寨门外椰子树上椰子累累,都爬上树去乱砍乱吃,把椰壳丢了满地。这时,总管却偷偷地钻进寨里,把每一家的门都打开来看。当他最后打开一扇门时,忽见茅屋中间地板上,坐着个织筒裙的姑娘,眼睛水汪汪,脸儿红艳艳,身材苗条,香气醉人,总管嬉皮笑脸地走近她的身旁。织着筒裙的邬珠,抬头看见进来的官爷,他鼻弯如鹰嘴,猴子眼睛骨碌碌地转,知道他不是好人,收起筒裙就往外走。总管见邬珠要走,伸手牵住她的衣裙。厚着脸皮说:“山茶花够好看了,比不上你好看;漂亮的姑娘我见得多了,却没一个比得上你漂亮,美丽的姑娘啊,我心里喜欢你,你就坐下来和我谈谈吧!”
邬珠见他动手动脚,气得大声骂道:“山猪的皮够厚了,比不上你这个做官的脸皮厚;乌鸦的声音够难听了,比不上你这个做官的话难听!黎家的娜邬从来和你们没交情,你为什么要这样无理缠人!”
邬珠的骂声全寨人都听见了,忙赶来看。邬珠的爹妈见到这情景,忙拱手向总管求情道:“我的邬珠年纪小,是不是她把官爷得罪了?请官爷看在我老俩口的面上,饶恕了她吧!”
总管见来的人多了,赶忙松手放开邬珠,冲着站在面前说情的邬珠爹妈,装着有礼貌地说:“两位老人不用害怕,不是你女儿得罪了我,而是我看上了她,我要把她带回官寨去。我的牛羊布满五指山,金银能填平冲山溪,你的邬珠嫁给我,不愁吃也不愁穿,要金随你挑,要粮随你搬,你老俩口是会答应的吧?”
听了总管的话,好像晴天里打雷,吓得老俩口半天才说出话来。邬珠爹说:“总管是普天下的官,邬珠是豪奥哇(黎语,意即穷人)的女儿,清水和浊水不相混,豪奥哇没福气嫁大官爷!”
邬珠妈说:“独女是爹娘的肉,独女是爹娘的心,邬珠绝不远离父母!”
总管见老两口推辞,把脸一沉说:“谁敢不听总管的话!我看上的人就是我的,你们不愿也得嫁!定下三天后来迎娶,若是邬珠有三长两短,我要你们的头!”说完就走了。
五指山后起黑云,台风也就快来到了。老两口听见总管的话,伤心得大声哭了。倔犟的邬珠,吐了口唾沫,骂道:“任他官大钱多,迷不住我的眼。我是豪奥哇的娜邬,绝不嫁给有钱有势的总管!”全寨人都同情邬珠,可是又惧怕总管势力大,都咬着牙走开了。
总管在番响寨的作为,传到了正在山上打猎的帕昂耳里,他急忙赶回邬珠家。邬珠一见帕昂,把事情哭诉一遍。
帕昂听了气得双眉倒竖,双眼闪光:“不是豺狼不黑心,不是总管做不出坏事!”说完,摸摸腰间的弓和箭,拔腿就要去赶总管。
邬珠看着心里急,一把抓住帕昂的手说:“帕昂哥,毒蛇窝里毒蛇多,官寨里头兵马多,你一个人去不顶事,怎能白白受人欺!”
帕昂听着急道:“难道你心甘情愿让他们抬去么!”
邬珠听了帕昂的话,哇哇地哭道:“槟榔能够破四块,椰树能够砍两排,我邬珠的心呵,死活也跟哥哥在一起!”
帕昂听着邬珠的誓言,流下了热泪。爹妈看着这情景,叹口气说:“台风刮起来了,要把房子压紧;总管的话已经说了,就得想办法对付!”
大家想了一整天,商量了一整夜,大计三十六,小计七十二,条条都想过了,没一条能够满意。邬珠双眉锁,心里暗思量:“总管要我不是为别的,只为我的容貌美,我要把容貌儿来改变,让总管死心!”
邬珠将这意见一说,大家听了都道:“红筒裙能够染成黑的,生就的容貌怎能改变?”
邬珠眉尖跳三跳,心头扎着一支针:“红筒裙能够染成黑的,生就的容貌也就能改变。黎家祖先手上能够刺黑纹,女儿的脸上也能刺上黑纹!”
爹妈听了邬珠的话,心里好比织乱麻:“手上刺黑纹,黎家有规矩;脸上刺黑纹,没有人做得出!”
帕昂听了邬珠的话,心象刀割一样:“筒裙脏了,一洗就干净;脸上刺黑纹,一辈子也擦不掉!可爱的邬珠呵,我怎忍心你把容貌改!”
好邬珠,忍泪劝亲人:“谁分不清好和歹,谁分不清美和丑,只因总管心肝黑,要把我呵来逼嫁。嫁到总管家,就像鸟儿入铁笼,见不到爹妈,见不到阿哥,见不到全寨众乡亲,苦水喝不完,闷气受不尽。我脸上刺黑纹,能保住我纯洁的心,能和爹妈、阿哥朝夕在一起,能保住全寨人的安全。”
爹妈听了悲痛地说:“我的好娜邬啊,你不这样做不行了!”
帕昂听了心疼地说。“我的好阿妹啊,你不这样做不行了!”
帕昂上高山,采回鸡藤荆;阿妈入菜园,采回青利树叶;浸水一天又一夜,浸出的水黑又黑。
晚上,邬珠跪在阿妈面前,阿妈手钳鸡藤荆,一荆一荆往邬珠脸上刺。刺一剂,一行泪;刺一荆、一滴血。刺得阿妈手发软,鸡藤荆从阿妈手中掉落了!邬珠咬紧牙,狠着心,从地上捡起鸡藤荆,一手执镜照脸,一手拿荆往脸上刺,刺得左脸两条痕,刺得右脸两条痕。帕昂端来青利水(用清利树叶浸出的黑水),慢慢往邬珠脸上擦,擦了一次又一次,擦了左脸擦右脸。两颊上显出了两条黑花纹;
爹妈看见了,两手掩着面,伤心地哭了。
帕昂看见了,用牙咬着嘴唇,血从口里流出来。
邬珠从镜中看见了,“哇”地一声喊,哭昏在地上。
第三天,总管迎娶邬珠来了,十二担酒肉和槟榔,十二担金银和衣裳。到了邬珠家,拿出绫罗纱缦,爹妈接来送进邬珠的房。邹珠不吭气,穿好绫罗纱缦,走出了草房。总管见邬珠,乐得像猴子,伴娘忙把邬珠扶进花轿,闹哄哄地抬回官寨去。
花轿一出番响寨,爹妈伤心地哭了:“我的好女呵,你离开了爹妈,爹妈见不到你,喝椰汁不甜,吃槟榔不香,你几时才能回到爹妈的身旁?”
邬珠一出番响寨,帕昂心里似火烧,端起火药枪,朝天上打了两枪:“邬珠给人抬走了,难道就这样作罢了?不成。我死活也要救邬珠。”他摸摸腰间的弓和箭,飞赶去救邬珠。
这天晚上,官寨里十分热闹,厅堂灯火亮,酒杯叮当响,总管喝得稀巴烂醉,走进新房。新房亮堂堂,邬珠站中央,纱慢罩在面上。总管一见邬珠,就伸手去掀纱。纱缦掀开了,总管的脸色变了样,邬珠怒目象闪电。脸上黑纹闪亮亮。
是酒醉花了眼,还是邬珠伤心的泪痕?总管心发慌,叫来了伴娘。伴娘手执灯,照近邬珠的脸;总管两眼象铜锣,直视邬珠的脸。可爱的邬珠,站着象云峰,两眼象闪电,黑纹闪亮亮。
总管看得清,总管心里烦,到口的肥肉落了地,气得乱跳,像只蟾蜍,管家的拿来了皮鞭,狠狠地抽打邬珠。皮鞭断了一条又一条,打手换了一个又一个。可怜的邬珠,被打得皮开肉烂,不能动弹。总管用脚踩了踩,怒道:“你不愿上天,就叫你下地!”说完,用眼扫了一下管家。管家背起邬珠。慌慌张张走出官寨。快走到河边,忽听近处响起脚步声,吓得他心惊胆颤,忙抛下邬珠,飞快地跑回官寨去了。
施风林中卷。黑云满天飞,帕昂飞赶救邬珠。一口气跑了三十里,还没赶到官寨。天已经黑下来了。天黑路难走,帕昂摸着走,只听野鸡山上啼,快到二更了,官寨的大楼也看得见了。
冲山河水响,帕昂的心事重,官寨里头兵马多,用什么法子去救邬珠?正想间,前面响起脚步声,出现一个大黑影。帕昂心里正惊疑,忽又听得一声响,黑影向着官寨跑。
帕昂急忙赶上去,看见草地上躺着一个人,俯脸定睛看,险些要晕倒。他用手摸摸邬珠的脸,摸摸邬珠的心,邬珠的脸冰凉,心微动。帕昂赶快跑到河边,用芭蕉叶盛回一包水,灌进邬珠的口,随后又解开衣裳,把她暖在怀里。
凉水透入心,邬珠睁开了眼;帕昂连叫数声,邬珠口里“腥”地吐出一团血。帕昂见邬珠醒了,伤心地说:“邬珠啊,你为我受尽了气,吃尽了苦,我没法子救你,让总管把你伤害了!”
邬珠抬起头,双眼闪着光:“青竹蛇算毒了,总管比它还狠毒!狠毒的总管呵,他可以打死我,却永远不能征服我的心!”
帕昂气愤地说:“邬妹呵,我们的仇要报,血要还!总有一天,我们要把狠毒的总管赶出五指山!”
帕昂背起邬珠,借着星光,一步摸一步,涉水又过山,鸡啼过三遍,他们回到了番响寨。爹妈见邬珠,眼泪滚滚流;全寨人听说邬珠回来了,都赶来看望。大家咬牙切齿地说:“有粮不缴官寨,有女不嫁总管!”全寨人都赞扬邬珠:“高山上的青松,台风吹不倒;我们的邬珠,总管折服不了!勇敢的邬珠,是我们黎家的好姑娘。”
台风打过了,天空晴朗朗,山上的苞麦,长得油油亮、苦难受过了,创伤养好了,可爱的邬珠,长得更美丽了。正是槟榔闪金光的美好季节。在一个悠静的月夜,冲山河水倒映着一对人影。
邬珠对帕昂说。“白衣沾上墨水,不好看了;我脸上刺着黑纹,不漂亮了。帕昂哥呵,我已经不配你了,你去寻找更美丽的娜邬吧!”
帕昂听着邬珠的话,激动地说;“邬妹呵,水晶石呵亮晶晶,比不上阿妹的纯洁坚贞!椰子水呵甜又甜,比不上阿妹的情意甜!你是鸟中的凤凰,花中的牡丹,你是五指山下最美丽可爱的姑娘!”
帕昂的话,像泉水冲洗着邬珠的心。她从衣袋里拿出口弦,轻轻地吹起了爱恋的歌;帕昂紧紧地靠着邬珠,和着口弦,唱起了幸福的歌!歌声冲破宁静的夜,全山寨的人都听见了,后生姑娘们,飞快地跑出山寨,跑到他俩身边,尽情地唱啊!跳呵!为他俩祝福!
不久,邬珠刺面的故事,传遍了五指山,人人疼爱邬珠,个个痛恨总管。姑娘们为了免遭总管和豪奥门(黎语,意即黎头恶霸)的迫害,学着邬珠,在脸上刺上黑纹。爹妈们为了女儿免遭总管的糟踏,学着邬珠,在女儿脸上刺上黑纹。从此,黎家妇女脸上刺黑纹的习俗,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了。
采录:陈永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