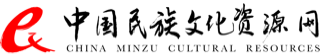《玛纳斯》: 柯尔克孜民族的灵魂
历史的足迹
1960年秋,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以下简称克州)乌恰县黑孜苇公社发现了《玛纳斯》歌手铁米尔、艾什玛特及一些史诗手抄本。
1961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同意由自治区文联、自治区文学研究所与克州党委宣传部联合组成史诗《玛纳斯》调查组。这次调查中,发现了能唱完整的8部20多万行的“玛纳斯奇”(《玛纳斯》的演唱者)居素甫·玛玛依。共记录史诗26万余行。
1964年,由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自治区文联、克州党委联合组成《玛纳斯》工作组。工作人员深入各地,搜集和记录了70多位“玛纳斯奇”的演唱,还搜集到《玛纳斯》手抄本21册,约9万余行。
“文革”开始后,工作组解散,工作被迫停止,居素甫·玛玛依演唱的记录稿汉文译稿散失,“文革”结束后仅找到部分残稿。
1978年,重组《玛纳斯》工作组。
1979年,在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主持下,在北京进行了近一年的记录和翻译工作,同年工作组撤回新疆。
1982年,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玛纳斯》工作领导小组,专门组织史诗《玛纳斯》的抢救工作。
到1995年,已记录《玛纳斯》史诗资料60多万行,出版了居素甫·玛玛依演唱的一至八部,共18册,同时出版汉文版《玛纳斯》第一部上下两册。
忧心的现状
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与我国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一起,被称为我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如今,《格萨尔》有多种版本的汉文书出版,而且还出版了《格萨尔故事集》,先后两次拍成电视连续剧;《江格尔》的汉文版先后由新疆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相关音像制品更是种类多样。而《玛纳斯》在至今出版的汉文版中最多也未超过5万行,与民间传唱的100多万行相比,相差甚远。很多《玛纳斯》史诗的各种变体连柯尔克孜文版都未曾出版,有些作过记录,还有些并未记录。民间歌手、“玛纳斯奇”以及“交毛勒奇”(民间故事家)、“库姆孜奇”(民间弹唱、说唱艺人)的录音、录像制品极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安东尼·克罗兹在谈到对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时说:“某些代表人物的消失,使得某种文化无法传承下去。”1961年《玛纳斯》工作组在调查时,全克州尚有百名能唱一至二部《玛纳斯》或大量不同变体的老歌手,至今健在者已无几人。特别是乌恰县的铁米尔、艾什玛特这两位老人,均因条件限制,他们所能演唱的二十几万行史诗,仅记录了几万行。
据调查,在《玛纳斯》的故乡克州,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学唱《玛纳斯》的青年人越来越少,使柯尔克孜族人民创造的这一伟大史诗的传承面临断代的危机。
生存的空间
笔者认为,如果建立一个《玛纳斯》史诗专题博物馆,让这些在民间流传千年的史诗,浓缩在一个既集中又高雅的殿堂之中,就会有一个充分展示的机会。这需要广泛搜集已出版的各种文字和版本的《玛纳斯》,录制“玛纳斯奇”和民间歌手在不同环境下演唱的录像,征集各种有关《玛纳斯》的传说、故事以及遗物,拍摄遗迹、遗址照片。通过现代光影技术,将史诗形象化地展示在人们面前。
在千余年的传承过程中,《玛纳斯》成为柯尔克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精神以及民族行为的规范。直到今日,柯尔克孜族同胞仍然希望男子要像玛纳斯一样,女子要像卡妮凯一样。因此,抢救、传承以至转型和发展,其实是在弘扬一种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民族文化。
《玛纳斯》史诗的转型也是拓宽生存空间的方法之一。它可以编排成音乐、舞蹈、戏曲等舞台剧,也可以改编成电影、电视,搬上银幕。转型带来的不仅是更多的听众和观众,还能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发展利用,取得一定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应当适时组织开展《玛纳斯》研讨会,联合中外学者共同把《玛纳斯》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开设专业网站;创办研究刊物。
应当申报《玛纳斯》史诗为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联合国的支持下,依靠国家的力量,做好保护和抢救工作。